那天晚上,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三点。电脑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生疼,文档上的字一个个我都认识,连成句子却读不懂意思。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漫上来,淹没了胸口,喘不过气。我甚至开始怀疑,是不是自己根本就不适合这份工作,是不是该认输了。
就是在那天深夜,我鬼使神差地给老周发了条微信:“周老师,我好像走到死胡同里了。”
老周是我大学时的老师,教设计理论的。毕业这么多年,我们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,偶尔会约着吃顿饭。他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,头发已经花白了,但眼睛总是亮的,看问题有种特别的透彻。
我以为这么晚他早就睡了,没想到手机很快亮起来:“胡同再死,墙也是人砌的。明天早上七点,老地方喝豆浆吧。”
第二天清晨,我顶着黑眼圈走进那家我们常去的早点铺子。老周已经在了,面前摆着两碗热气腾腾的豆浆,一碟油条。他什么都没问,只是推过一碗豆浆:“先喝点,暖胃。”
等我喝了半碗豆浆,身体暖和了些,他才慢慢开口:“说说吧,什么样的胡同?”
我一口气把项目的困境全倒了出来——客户苛刻的要求、团队创意的枯竭、一次次被否定的绝望。说到最后,声音都有些发抖:“我觉得我们已经试遍了所有可能的方向,真的无路可走了。”
老周安静地听着,用油条蘸了蘸豆浆,不急不缓地吃完了一根。然后他抬起头,看着我的眼睛:“你刚才说,试遍了所有可能的方向?”
我用力点头。
“那不可能的方向呢?”他问。
我愣住了:“不可能的方向……为什么要试?”
“因为当所有‘可能’都走不通的时候,‘不可能’就成了唯一的可能。”老周笑了笑,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,“给我讲讲,你们认为最不可能的那个方向是什么?”
我想了想:“有一个特别大胆的构想,完全颠覆行业常规,但风险太大,我们第一次讨论就否决了。”
“为什么否决?”
“太冒险了,万一失败了,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客户那么保守,肯定不会接受。”
老周往椅背上一靠:“你看,你们给自己砌了两堵墙:一堵叫‘万一失败’,一堵叫‘肯定不会接受’。还没开始砌第三面墙,就已经把自己关在里面了。”
这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是啊,我们甚至没有认真论证过那个构想,仅仅因为它看起来“不可能”,就自动放弃了。
“这样,”老周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,“咱们今天不聊怎么让这个构想成功,就聊聊它如果失败了,最坏能坏到哪里去。你把所有能想到的坏结果都写下来。”
这个角度太奇怪了。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,我还是接过了本子。写着写着,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——那些想象中的“灾难性后果”,其实大多都有应对的办法。最坏的情况,也不过是项目真的换人,而这一点,本来就要发生了。
“看来天塌不下来。”老周看我写完了,笑眯眯地说,“那现在,咱们聊聊这个构想如果成功了,最好能好到哪里去。”
就这样,在那个飘着豆浆香气的早晨,老周带着我完成了一次思维上的“倒立”。不看高处怕摔跤,先看摔了会怎样;不急着证明自己能行,先承认哪些地方不行。当我把所有最坏的结果都摊在阳光下审视之后,心里的恐惧反而消散了。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我带着团队重新捡起了那个“不可能”的构想。不一样的是,这次我们做好了充分的预案,对每一个可能被质疑的点都准备了扎实的数据和案例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不再试图说服客户这是一个“完美无缺”的方案,而是坦诚地告诉他们这是一个“大胆的尝试”,同时详细说明了风险控制和备用方案。
汇报那天,我平生第一次在提案时如此平静。不再绞尽脑汁地掩饰缺陷,不再过度承诺效果,只是客观地展示我们的思考。出乎意料的是,客户对我们坦诚的态度非常欣赏,那个曾经最保守的副总甚至说:“等了这么久,终于等到一个不一样的思路了。”
项目通过了。不仅通过了,后来还成了公司的标杆案例。
庆功宴那天晚上,我又去找老周。这次是在他家的小院里,夏夜的风吹着葡萄叶子沙沙作响。我给他带了一盒好茶,由衷地说:“周老师,真的谢谢你。要不是你,我可能已经放弃了。”
老周摆摆手,给我倒了杯茶:“我什么也没做,只是陪你喝了碗豆浆。”
“可是你教我的那个方法——”
“那不算什么方法,”他打断我,“就是活得久了,明白了一个道理:人害怕的不是困难本身,而是对困难的想象。你把想象具体化,它就没那么可怕了。”
他指着院子里的一盆兰花:“你看这花,前段时间生了病,叶子都黄了。我要是天天对着它愁,它也好不了。后来我就想,最坏不过重新种一盆。这么一想,反而静下心来,该换土换土,该施肥施肥,你看现在,不是活得好好的?”
我忽然明白了,老周最厉害的地方,不是教了我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,而是在我最慌乱的时候,给了我一种“定”的力量。他让我看见,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,当你走近了、摸清了,其实都有跨过去的可能。
后来这些年,每当我遇到看似无解的难题,都会想起那个早晨的豆浆铺子。我会学着老周的样子,先停下来,喝杯热茶,然后把问题拆开来看:最坏能怎样?最好的可能又是什么?现有的资源有哪些?一步一步,不急不躁。
老周去年退休了,搬到了郊区的院子里住。我偶尔周末去看他,帮他侍弄侍弄花草。他还是老样子,话不多,但每句都能说到点子上。上个月我去的时候,带了自己做的绿豆糕,他尝了一口,点点头:“火候刚好。”
坐在那棵越来越茂盛的葡萄架下,我想,人生大概就是这样——我们都会遇到自己的死胡同,都会有无助的深夜。而最好的帮助,有时不过是一碗热豆浆,一个愿意倾听的人,和一句:“来,咱们看看这堵墙是怎么砌的。”
老周从没说过什么高深的理论,但他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一件事: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死胡同,只有还没找到的出口。而找出口的第一步,往往是先承认自己迷了路,然后安静地坐下来,看清周围的环境。
那个项目的成功早已成为过去,我在职场上遇到了更多、更复杂的挑战。但每当压力山大、觉得无路可走时,我都会深呼吸,然后问自己:老周会怎么说?他大概会慢悠悠地倒杯茶,说:“急什么,天还没黑呢。来,先把眼前这步走稳了。”
是啊,急什么。难题还在那里,但心定了,路自然就显现了。这就是老周给我的,最可靠的帮助——不是直接给我答案,而是陪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题方式。这份从容,让我受用至今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东科创业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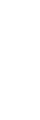 东科创业文章网
东科创业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62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61)
2带新人的过程:我反而补全了自己的能力短板阅读 (60)
3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58)
4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58)
5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