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磕磕绊绊打到每分钟十个字,到如今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每个按键的位置,这双手在键盘上走过的路,可能比双脚走过的还要长。大学时在网吧通宵赶论文,键盘缝里卡着烟灰;刚工作时用笔记本写方案,咖啡洒在空格键上;现在给孩子讲故事时,她总喜欢用肉乎乎的小手乱按,Delete键上还留着她的牙印。
真正开始用键盘做翻译,是帮邻居老陈读他在美国儿子的信。老陈不识字,每次收到电子邮件都要跑到打印店请人打印出来,再找我念给他听。有次店里打印机坏了,我索性直接在电脑上给他读。老人凑在屏幕前,浑浊的眼睛随着光标移动,仿佛这样就能离儿子近些。那封关于孙女生日的邮件,我念了三遍,他听了三遍。
后来我开始接些零散的翻译活儿。最难忘的是给一位抗战老兵整理口述史。老人浓重的湖南口音让我不得不反复确认,每当翻译到惨烈的战役,他的手指会无意识地在桌上敲击,像在发电报。我把这些细节都写进译文里,包括他停顿时的哽咽,回忆战友时突然哼起的军歌。交稿后,他女儿来信说,父亲对着翻译稿哭了整整一夜。
键盘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。凌晨三点翻译情书,"我爱你"三个字斟酌了半小时;帮留学生翻译家书,把"我很好"背后的哽咽也译出来;甚至翻译过遗嘱,光标在财产数字前停留许久,仿佛能看见老人写下这些时颤抖的手。
有年冬天接了个急单,是给癌症晚期患者翻译国外医疗方案。患者家属每隔一小时就发消息问进度,我在书房坐到凌晨,键盘声像秒针滴答。完成时天刚蒙蒙亮,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,突然听见窗外早起的鸟儿在叫。那个冬天后来患者奇迹般好转,家属寄来感谢卡,我把卡片压在键盘下面,继续翻译下一个文件。
最奇妙的经历是翻译一本童话。为了找到"月光穿过树梢像撒了一把碎银子"的恰当表达,我带着键盘去公园的长椅上工作。孩子们围过来看我在做什么,我就把翻译的故事念给他们听。现在这本书放在本地图书馆,偶尔会看见有母亲读给孩子听——用我敲打出来的中文版本。
键盘也有沉默的时候。疫情初期翻译防疫指南,每个数字都重若千钧;翻译离婚协议时,当事人要求把"祝你幸福"译得尽可能温柔;最难过的是翻译宠物墓志铭,短短三行诗,眼泪把键盘都打湿了。
这些年,键盘换了好几个,从机械到静音,从有线到蓝牙。但始终保留着最初那个油腻的旧键盘,Back键被磨得发亮,像时光打磨的鹅卵石。它记得我翻译第一封情书时的心跳,记得我收到第一笔稿费时的雀跃,记得每个深夜里,文字如何像萤火虫在屏幕上次第亮起。
也许到很老很老的时候,我还会坐在摇椅上敲键盘。可能是在翻译孙子的作业,可能是帮老伙伴读海外亲友的来信,也可能只是把一生的故事都敲出来。让每个字都带着温度,就像当年老陈说的:"小丫头,你敲键盘的声音,听着就像在说话。"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东科创业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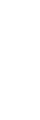 东科创业文章网
东科创业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59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57)
2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55)
3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54)
4带新人的过程:我反而补全了自己的能力短板阅读 (54)
5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